海克尔曾说,一门科学若满足于描述、列举和编目那些在感知中即刻呈现的事物,便沦为琐碎的实证主义;他举博物馆系统分类学者满是标本的积尘抽屉为例,这些标本虽标签齐全却无一被理解,正是此类无意义知识追求的典型。 海克尔志在探究宏大问题,他引用了备受尊敬的胚胎学家卡尔·恩斯特·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后者在其1828年关于动物发育的经久不衰的专著副标题中强调“观察与反思”,认为二者必须相辅相成,科学方能结出硕果,产生引人入胜的见解和成果。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经典主题,海克尔在推崇这位德国哲学不朽巨匠的同时,将其应用于他所钟爱的前瞻性实证主义视角,而非回顾性的康德式观点。对康德而言,感官经验直接把握的仅是直观(Anschauung),非知识,因为“无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无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纯粹的观察——即便可行——也只能产生缺乏意义或上下文联系的表象混乱,这显然不足以支撑科学。康德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探寻自然中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将揭示支配它们的法则。真正的、有趣的科学最终关注的是发现自然的普遍法则,而这些法则最好能以数学语言表述。 对康德而言, 自然科学的手臂延伸至其能以数学方式把握自然的极限。而海克尔则认为,这些自然法则必须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而非空洞的形而上学推测之中。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生物学界确实兴起了一股反对理想主义自然哲学的浪潮。柏林大学教授、自诩为歌德信徒的约翰内斯·穆勒(Johannes Müller),尽管深知科学实验的陷阱与局限,仍被誉为德国生物学比较生理学之父。除了格根鲍尔和海克尔,他的学生还包括马蒂亚斯·雅各布·施莱登(Matthias Jacob Schleiden 1804-1881)、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埃米尔·杜·博瓦-雷蒙(Emil du Bois-Raymond 1818-1896)以及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等名人。1833年约翰·F·梅克尔(Johann F. Meckel)去世后,约翰内斯·穆勒接手编辑《解剖学与生理学档案》(Archiv für Anatomie und Physiologie),并自1834年起将其更名为《解剖学、生理学及科学医学档案》(Archiv für Anatomie, Physiologie, und wissenschaftliche Medicin)。1838年,他安排在其期刊上发表了施莱登的发现,即所有植物的发育均始于一个细胞,这是迈向细胞理论的第一步,该理论将永远改变生物学的面貌。施莱登在其开创性论文的开篇便提出一个康德式的关注点:“人类推理的普遍法则,即在其发现中不懈追求统一的法则,同样在生物界显现”:认知的统一性体现在最终源自单一细胞的植物统一性中。对施莱登而言,细胞是生物个体的典范;由它发育而成的整株植物是个体的集合。植物生长是有规律的,即必然是细胞增殖的结果。施莱登承认在植物界存在显微镜下无法直接观察到细胞形成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该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因为这是类比所要求的,且我们能充分说明这种直接观察不可能的原因。”当施莱登将他的发现告知同窗特奥多尔·施旺(Theodor Schawnn 1810-1882)时,后者也传达了他在动物组织中类似的观察结果。这次交流的成果便是“施莱登-施旺”细胞理论,约翰内斯·穆勒迅速将其融入教学中。菲尔绍随后于1858年以“一切细胞来自细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的口号推广了细胞理论,并将病理现象归因于细胞功能障碍。
施莱登在其1842/43年的重要著作《科学植物学基础》(Grundzüg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Botanik)两卷本中,阐述了他对现代植物学的愿景。他在书中对当时植物学领域盛行的两种趋势表明立场:一种是植物学家仅看重物种描述本身的价值,对国内外植物多样性进行编目而缺乏进一步综合;另一种则是沉溺于缺乏实证基础的“自然哲学”式臆测。 他的论文开篇即阐述了科学植物学应有的哲学基础,这一基础被海克尔誉为如同约翰内斯·穆勒对动物学的革新一样“开创性” (pathbreaking)。 施莱登致力于将植物学构建为一门彻底归纳性的科学,在此过程中,他重新采纳了冯·贝尔的“观察与反思”主题,海克尔后来也以极大热情追随了这一做法:
未经实证调查,未经观察,便不可能有实证科学,但一堆赤裸裸的事实远非科学,正如单纯的砖瓦成不了庙宇。 超越观察所需的,是将可疑与确凿、偶然与本质区分开来,是推导规则与法则——所有这些皆为纯粹的观察所不知且无法知晓的智力操作。
施莱登意图将因果分析置于科学植物学的核心地位,这一主张得到了海克尔的赞赏,他援引施莱登的《科学植物学基础》来支持自己关于科学划界于形而上学的观点。 施莱登强调,每位科学家都必须接受哲学训练,尤其是逻辑学,并秉承培根传统(Baconian tradition 归纳排除法),宣称科学探究既可从特殊归纳至普遍,亦能从普遍演绎出特殊。 正是这种上下求索的互动,成就了物理学上的伟大发现。“然而,若将形态学科学与物理学理论相比,”施莱登继续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前者远远落后。”这不仅是因为比较解剖学所处理的生命复杂性难以用数学分析,更普遍的原因是对“方法论、概念及一般哲学”分析的忽视。海克尔对此深表赞同,并进一步巩固了他对何为或应为何为真正科学探究的看法,他再次求教于其著名导师——19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生理学家与形态学家”约翰内斯·穆勒。穆勒在其1840年出版、极具影响力的《人类生理学手册》(Handbuch der Physiologie des Menschen)中,将引力与惯性列为物理学的典范定律。但引力的本质,即其实质或力学基础——一种超距作用力——究竟为何?穆勒提及“安德烈-马里·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 1775–1836)为发现自然定律奠定了基础,从这些定律出发,电磁现象可以如同几何真理从其基本公理演绎而出一样被确定地推导出来……然而,电的本质仍难以捉摸。”穆勒断言,神经支配的机制、细胞生命的机制、植物和动物发育的机制以及心理过程的机制也是如此。不过,不了解自然因果关系的实质——即物质基础——并不妨碍科学从经验观察中归纳出具有预测能力的定律。穆勒进一步指出,科学不能仅靠概念上的哲学分析推进,单纯的观察也不足以支撑其发展。相反,需要的是一个能构建感官经验的概念框架,以区分偶然与本质,即对经验进行哲学化处理。海克尔从马蒂亚斯·施莱登和约翰内斯·穆勒这些权威且基础的教科书中得出了几项主要结论: 科学是关于自然定律的发现;归纳与演绎是获取科学知识的互补途径;即便现象的复杂性尚未允许以数学形式表达这些定律,自然仍可展现规律性;即便过程背后的力学机制尚未(完全)明了,定律仍可具备预测能力。 海克尔将如此构想的科学称为“哲学经验主义”或“经验哲学”,两者均源于观察与反思、“自然描述”与“自然哲学”之间密切的相互启发。对海克尔而言,这样的哲学基础似乎是使适用于生命实体的发展思想(Entwicklungsgedanke)触及科学之臂的唯一途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海克尔答曰:是的,但不是谢林或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 1779–1851)所表达的那种“自然幻想”(Naturphantasterei)意义上的。海克尔以概念分析和分类的方式回应德国唯心主义,构建其自然哲学。分析与综合是通向科学发现的两条互补道路,分析关注特殊与个体,综合则关注普遍与涵盖同类个体的定律:“唯有通过综合,最重要的普遍定律才会显现,这些是分析永远无法带来的洞见。”正如施莱登所主张的,归纳与演绎同样是相互启发的推理方法。归纳通过比较与概括从特殊上升至普遍陈述,随后由演绎加以验证。在此意义上,归纳开启科学探究,演绎则为其画上句点。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它们之于科学理论构建,犹如吸气与呼气之于生命——这是海克尔采纳的众多歌德式隐喻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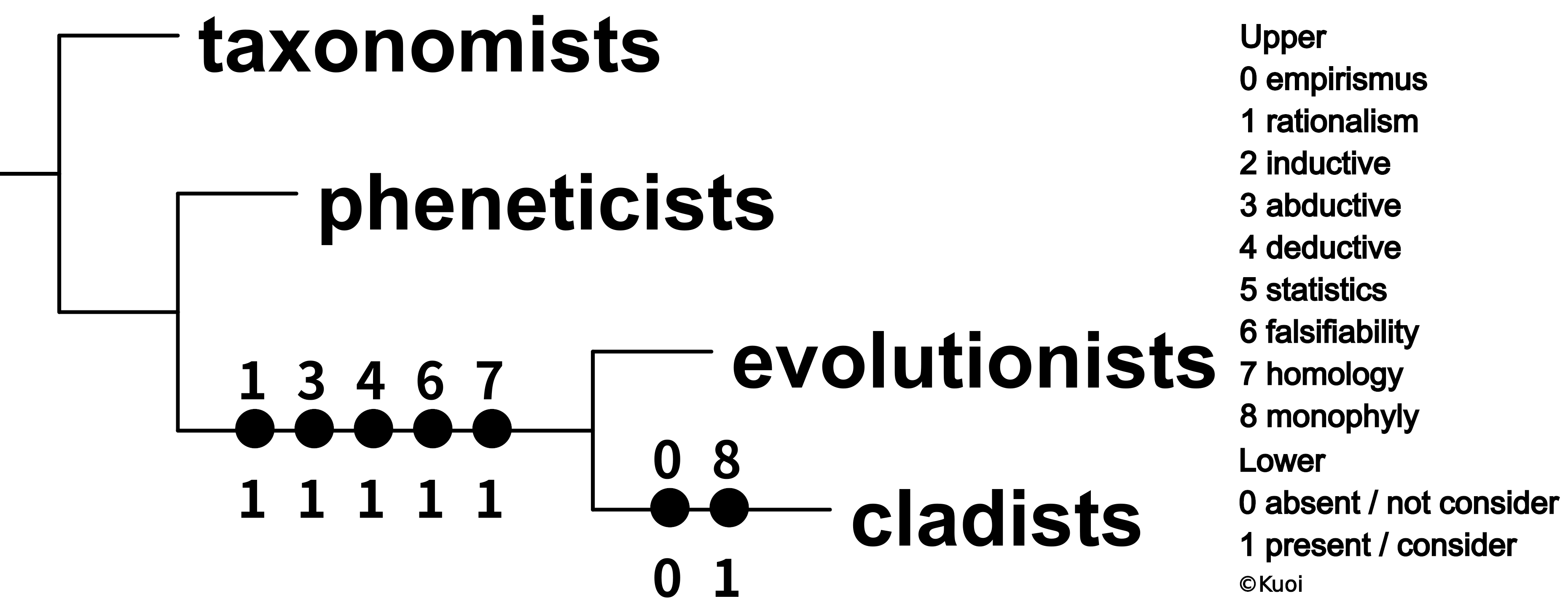
Comments
No comments yet. Be the first to react!